口蘑小志
—口蘑的口字就是张家口的味儿
客居外乡,与人闲谈,方知不少人不晓这“口”字竟指张家口。家乡风味未能广知,或是吾辈乡人未尽心力。
须知此“口”非彼口,乃张家口之“口”。 缺此一“口”,长城如断齿;缺此一“口”,草原似绝途;缺此一“口”,菌伞亦无根——口蘑者,张家口之魂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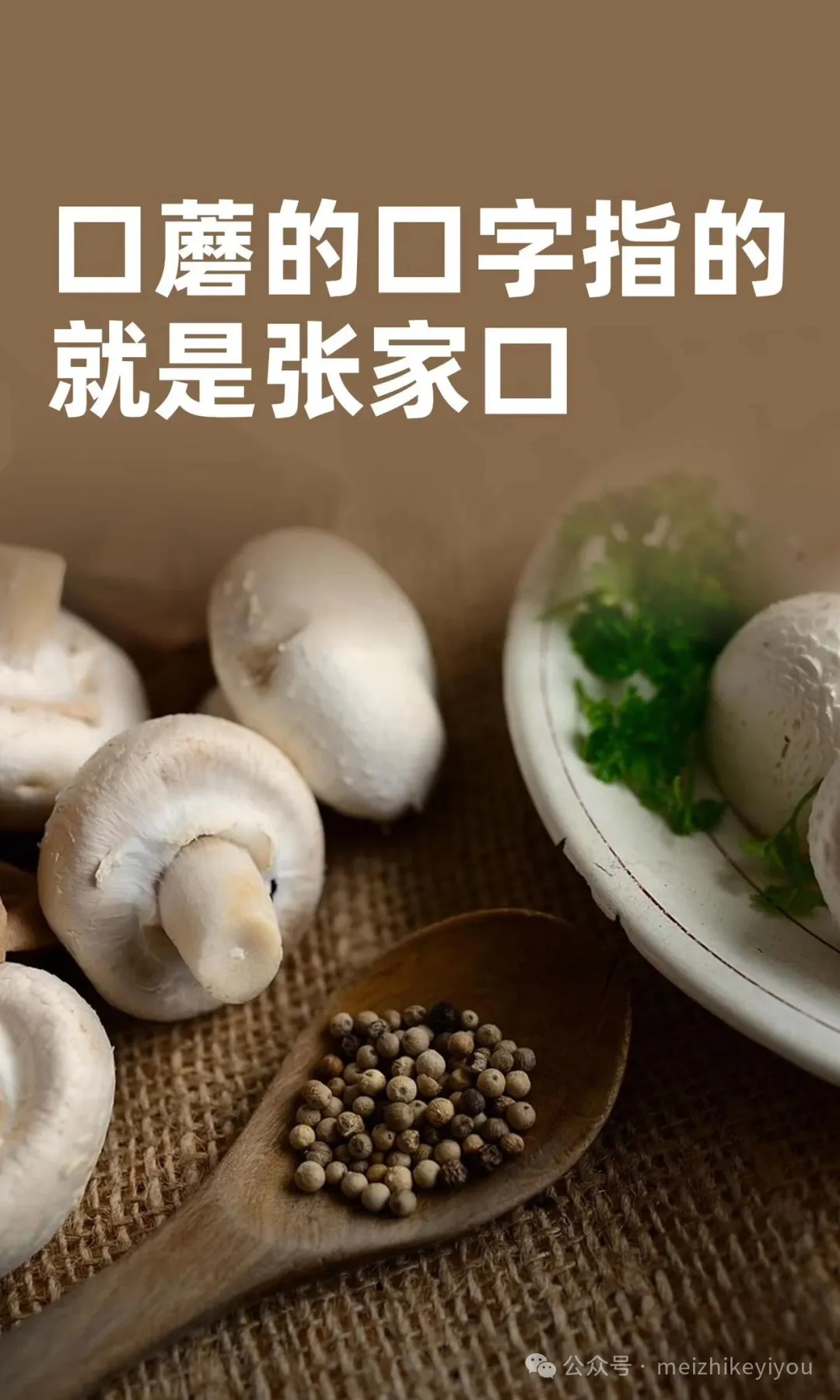
“口蘑”之名见诸文字,最早的踪迹可循至清乾隆二十三年的《口北三厅志·物产》:“蘑菇,出张家口外草地,色白而香,商贾捆载南售,呼曰口蘑。”寥寥“口外草地”四字,已将产地钉死在张家口以北的坝上高原;“商贾捆载”一句,又把这点塞北山野的灵气送入了帝都九门。自此,“口蘑”成了它响当当的名号,前头不必赘加“张”“家”二字,天下人也认得了它的出处。
同此命运的,还有口羔与口皮:口羔者,坝上六月催肥、九月宰杀的羯羊;口皮者,取此羊羔之皮鞣制而成,白似新雪,轻软异常。三样土产齐聚,才算是张家口完整的气象筋骨。
口蘑生于坝上。坝上地方高寒,一千三百多公尺,六月的天,夜里飘点雪星子也是常有的事。苔草、金莲、野百里香密密地长着,牛羊踩过,留下温热的粪肥。菌丝儿得了这点地气暖意,一夜之间,便撑开了圆圆的小伞。采蘑人得赶在天蒙蒙亮以前,提着马灯出帐。昏暗的灯影里,一朵朵新蘑从草丛钻出,真像散落一地的小月亮。采进柳条筐,要轻拿轻放,万万压不得——这股山野的灵气,最是怕压。采下便摊开在芨芨草编的长席上,白日里尽晒着毒日头,夜里承着冰凉的露水,如此几天几夜,直晒得干透透的。干的极好的口蘑,用手一折,“嚓”地一声脆响,碎末里透出一股松林气混着奶酒的幽香——你闻闻,这是不是草原写给张家口一封带着水汽、沾着草屑的情书?
张家口人做口蘑,不弄那些花巧排场,只需一锅热腾腾的“口蘑羊肉汤莜面鱼鱼”。做法上,也分三段功夫:
吊汤:
- 羯羊后腿带骨砸断,冷水下锅撇沫,加姜片、花椒、葱白,文火三小时,汤浓似乳。
发蘑:
- 干蘑去蒂,温水泡于敞口老磁碗。半小时后换水,须用力搅动揉搓(轻轻不行!),令藏沙尽落。 再泡半时,水色清透如淡珀,蘑体饱满弹软,即成。发蘑水澄之,取上层清液入羊汤, 草原山菌与长城羊鲜,于此交融。
烹鱼鱼:
- 莜麦炒熟磨粉,沸水烫面,趁热搓成两头尖、肚儿鼓的麦穗鱼儿。鱼鱼儿须上笼蒸熟(此为三熟之精髓),出笼晾温后,手指轻捻抖散,根根分明。 食前,取蒸熟抖散的莜面鱼鱼入滚沸羊蘑汤,汤色金红,乌玉蘑片沉底,晶莹鱼鱼儿浮沉。
先喝头口汤。羊汤的厚腴、野蘑的鲜纯、胡油的焦香,三股劲头齐驱并驾。再咬一口蘑菇,肉厚且糯,汤汁充盈,稍一咀嚼,仿佛齿间碾破了草原的清露。最后捞一尾鱼鱼儿,莜面筋道弹牙,裹着浓汤油花,“哧溜”吸进口中,一股暖意能顺着喉咙下到脚指头。张家口人讲究这一口叫“连汤带水”。老话说得好:“连汤带水,一冬不冷!”
我生在大境门下,父母皆喜读书。大境门砖缝里的碱草,春绿秋黄,是我童稚岁月的年历。家中书卷琳琅,而我除了那些字纸,最关心的便是每顿吃食。隆冬清晨,父亲推门买羊肉,母亲将干口蘑轻置老磁碗,我趴在炕沿背诵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”,却被蘑菇在水中舒展的簌簌声打断——那声音,像极了细碎雨点落在草原上。
三岁那年印象尤深,父亲巧手剪硬纸板,不多时便为我制出一套识字卡片。因着当日食谱,我便从中先识得“口”与“蘑”。冬夜随父母学搓莜面鱼鱼,母亲吟诵《诗经·七月》“朋酒斯飨,曰杀羔羊”,父亲应和一句“有洌氿泉,无浸获薪”,锅里的汤咕嘟应声。那一刻,口蘑的鲜、羊肉的醇、莜面的韧、诗句的雅,连同那塞外的风,便一齐融进了我的骨血。
这块土地上的故事,数不尽数:有远古炎黄与蚩尤阪泉的烟尘,亦有黄蓉与郭靖初见的缘起;有明英宗黯然困锁的“北狩”身影,有康熙爷凯旋却吃闭门羹于大境门下的小插曲;也见证着冯玉祥、吉鸿昌们在此擎起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大旗……千年故事,都汇在此一方“口”内。
后来负笈远游,尝遍四方滋味。江南的三虾面鲜甜细腻,山城的豌杂面浓厚热烈,都是好味,却始终不是家中那一碗汤的韵脚。有时午夜梦回,恍惚又站在大境门脚下,总觉枕畔萦回着自家胡诌的一句:
“长城一口吞风雪,吐作人间蘑菇香。”
零九年,漂泊日久,才在北京城安顿下来,勉强算作依傍在故乡门口。正巧一旧友自美洲归来,一时不及返乡,便引了他去“西北莜面村”——不能带你归家,权且让这一席家乡风物做个引子吧!
只是,那顶好的口蘑,如今真是可遇难求了。离了那坝上湛蓝的天、碧油油的草、还有那水质硬朗得咯牙的水土,哪还养得出我们张家口这品性的——“楞楞”口蘑。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